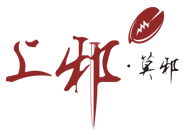簡介
面對不斷上升的基尼系數帶來的問題,中國政府仍然覺得有充分的時間來應對。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文化中對于貧窮的認知:在中國,貧窮是不體面的。(相反,在其他有很多窮人的社會裏,如印度,窮人並不為自己的貧困感到羞恥)在中國,窮人不願意抛頭露面,或者被告知不要抛頭露面,他們會因為自己的狀況感到 “丟臉”。這種窘境帶來兩種影響:正面的影響是,它推動人們去擺脫貧困,去進行商業冒險;負面的影響是,那些被長期被置于貧窮狀況的人會心生怨恨,從而導致抗議、騷亂甚至引發革命(當然,革命的後果並不總是負面的)。
那麽革命會發生嗎?未來會怎樣?作者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解讀。
面對不斷上升的基尼系數帶來的問題,中國政府仍然覺得有充分的時間來應對。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文化中對于貧窮的認知:在中國,貧窮是不體面的。(相反,在其他有很多窮人的社會裏,如印度,窮人並不為自己的貧困感到羞恥)在中國,窮人不願意抛頭露面,或者被告知不要抛頭露面,他們會因為自己的狀況感到“丟臉”。這種窘境帶來兩種影響:正面的影響是,它推動人們去擺脫貧困,去進行商業冒險;負面的影響是,那些被長期被置于貧窮狀況的人會心生怨恨,從而導致抗議、騷亂甚至引發革命(當然,革命的後果並不總是負面的)。
有一種非常普遍的認知:認為街頭抗議只是第一步,其必然導致騷亂和暴動,最後不可避免地引發革命。這是一種誤導,因為抗議與革命有本質的區別。革命需要的不僅僅是改變現狀的沖動,它需要方向,需要解決“往何處去”的問題。“往何處去”,這恰恰是最令人困惑的一個問題,不管是對中國,還是對其他國家來說。
大部分西方人希望看到一場民主革命。但民主本身只是一個程序,它並不能指明從這個程序中將産生一個什麽樣的政府:可能是自由派或保守派;可能是基督徒或世俗論者;可能是民主派或共和派。有一種正在中國的窮人中蔓延的思想是新毛澤東主義,但是它的前景並不樂觀。畢竟,毛澤東主義曾經統治了中國30年,留下了許多失敗的創痕。中國的窮人們在尋找其他思想,而許多其他宗教比新毛澤東主義更受歡迎。比如當前的法輪功,和其他一些僞基督教組織(它們像以前的太平天國)。
一些類三合會組織也做的不錯。他們通過威脅和賄賂控制了許多村莊的選舉。他們也幫助組織流動工人到城市裏從事體力勞動。關于新毛澤東主義、新興教會和三合會的影響的社會學研究還非常少。但是,一份對北京普通外來工的隨機調查顯示,他們對上述團體的熟悉程度遠遠勝過西方的民主制度。針對這個事實來,有人可能會說:如果中國發生革命,將會是一場類宗教的革命,或一場三合會運動。這不是不可能的,中國曆史上的大多數王朝,包括現在的“共産黨”王朝,都帶著某些宗教的特征。
但總得來說,中國人已經受夠了革命,在過去的160年裏,他們有過太多。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盡管仍存在社會差異,從絕對意義上來說,生活水平提高了。僅僅15年前,北京的學校食堂裏仍在提供營養不足的食物,現在再也不會了。另外,社會流動性也大大增加。你有更多的機會送孩子讀大學,或開始一場商業冒險。最後,那些陳舊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奮鬥路線”也消亡了:窮人不再要消滅富人;無産階級也不再是社會的領導階級;而知識分子要麽謀取官職,要麽下海經商。
正在現代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中國,每個人似乎都反對其他人。這顯然不是一個適合革命的時機,卻要求中央政府不斷地調節各個階層的利益:富人看不起窮人;中産階級反對所有其他階層;中央與地方有矛盾,各地市也與省政府不完全一致。所有這些長期存在的沖突都要求中央政府比二十年前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介入。從前,一切都很清晰:黨的領導人們擁有一切,其他人一無所有。領導者被孤立,也因此一度被圍攻。社會階層的區分非常清晰:那些沒有政治權利的人,包括學生、工人、農民有潛在的可能團結起來,去反對那些握有權力的官員。
今天的情況變得非常模糊。現在有的人有權沒錢,有的人有錢沒權,有的人既有權又有錢(那些貪汙的官員)。現在有富人,中産階級,城市裏的窮人和農村的窮人(這兩種窮人是非常不同的,有著完全不同的目標)。根據社會身份的不同,還可以分為學生、官員、企業老板……。總之,整個社會已經變得更加複雜,政府要在所有事情上保持平衡變得非常困難,但這種情況也創造了廣闊的空間讓政府去運作,一個20年前不存在的空間。政府不得不練習使用它的權力去平衡,而不是像從前那樣根據階級劃分來規定所有事情。
社會階層的多樣化,客觀上使開展一場革命變得更加困難。哪個集團能領導一場雄心勃勃的革命呢,工人?農民?讓他們聯合起來共同領導應該是不可能了,因為他們各自的利益要求差別很大。的確,有些知識分子考慮過組織一場農民運動,有些人甚至到村莊去動員農民,一些農民也曾經到城市裏尋求知識分子的幫助。事實上,這種活動已經持續了一些年頭,但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實質的進展。這顯然不是因為似乎無處不在的中國安全機構,真正的原因是:革命的前提不曾存在過,現在仍不具備。
此外,政府公開地揮舞著基尼系數也表明:今天的社會差異是社會透明度的一部分。而在毛時代,社會差異非常極端,但被隱藏起來了。在毛時代,政府官員們被系統地分層級(當然,“偉大舵手”自己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各層級都對應著各自的“待遇”,一個用于區分不同程度特權的技術用語。從金錢上來說,各層極的差別並不大,不過在這段“正統”共産主義時期,金錢反正什麽也買不到。國家領導人在每個省都有自己的別墅,配有傭人和廚師,這些別墅隨時候命,盡管它們的主人可能永遠都不會去其中一些地方。部長們享有很大的房子,並配有司機。處長和局長們有私人轎車和電話。與此同時,人民常常挨餓。這種特權是靠保持神秘感來維持的——沒有人可以細查這些領導人的日常起居,他們生活在重牆深院後面。今天,北京的街上仍然跑著一些帶彩色車窗的轎車,這是那段曆史的遺産。那時,國家領導人坐在巨大的紅旗車裏,飛快地駛過荒涼的長安街。跟現在相比,那時的社會差異是如此的大。
但是,那時的社會差異是隱藏的,而現在是公開的。非常普遍,兩個曾經過了幾年同樣生活的人現在的經濟差距可能非常大:一個仍在騎自行車,一個在開寶馬。和諧社會的一個理念就是,人們必須接受這些差異。這些差異,少部分是官員貪汙的結果,但大部分還是由于個人的商業才能或其他天賦。
看起來,中國政府仍然自信它能控制局面。社會的變化給了現政權更大的機動空間。而現在這種巨大的社會透明度,實際上提高了政府保持控制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假使政府推動自由化,或邁向民主,它實際上能夠贏得更多的擁護和支持,而不是更少。也就是說,將來我們可能看到中國社會變得更加透明、自由與民主,同時中國共産黨的影響變得更大。在某些觀察家眼裏,這個結論自相矛盾。他們不會明白,除非他們學會不把中國共産黨看成是“共産黨”。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方面來看:曆史上所有對黨的權力的重大沖擊都不是來自敵對勢力,而是來自黨內。已故的趙紫陽先生是黨的總書記,他現在被尊為自由的化身。異議人士的領導者鮑彤是他的秘書。甚至在法輪功事件裏面,1999年組織法輪功學員在中南海靜坐示威的(引發政府恐慌,隨後進行鎮壓)也是黨的資深官員,包括一位後來被判有期徒刑13年的退休空軍將領。
現在的情況仍是這樣,黨控制了一切。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組織、宗教團體或三合會能夠挑戰它。某些三合會勢力強大,與政府官員與警察有密切的關系。但它們的影響力只限于所在的省份,通常是所在的城市。即使是天主教(他們幾十年來一直效忠羅馬教宗,抵抗共産黨的打壓),他們很團結,也很有組織。但他們只能影響信徒,影響不了其他群衆。另外,這些團體還互相競爭:天主教當然反對三合會,三合會組織之間也互相爭奪,其他農村的教會也是如此。
即使黨不能把所有的社會團體置于它的嚴格控制下(它一直非常渴望這麽做),對于這些社會團體來說,想要勝過黨或其他競爭團體是很困難的。事實上,由于各種原因,這些社會團體更願意與黨共存,並避免公開挑戰它。這種情況,就導致了那幾百萬抗議示威的民衆陷于孤立。所以,引發政治劇變的唯一可能性在于:某次黨內的重大權力鬥爭突然公之于衆。就像在天安門事件中發生的那樣。或者在某種程度上,鎮壓法輪功事件也是如此。
這樣的內部權力鬥爭將再次發生嗎?局外人誰也說不准。但是,黨已經從天安門事件,和導致1991年戈爾巴喬夫下台的蘇聯政變中吸取教訓:如果內部的權力鬥爭曝之于衆,輸的將是黨內所有人,而外部勢力可能乘機介入奪權。在某種程度上,對這個事實的理解在1992年楊尚昆集團的讓位中初現端倪,在1995年逮捕位高權重的北京市市長陳希同時得到貫徹,並使1997年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離開權力成為可能,從而為李鵬( 原文此處為Jiang Zemin, 應是筆誤 —— 譯者)騰出位置。
在鎮壓法輪功事件中,許多資深退休老幹部站出來表示同情。黨聚集了所有力量把這些人都推回去,避免了大規模的黨內沖突。從所有這些事情中,黨已經學會了很多,它甚至可能領悟到:真正的威脅不在于城市裏遊行的那幾百萬人,而在于黨的高層。
來源:譯言 翻譯: All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