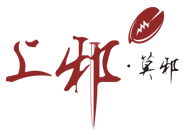自八月下旬以來,“輿論鬥爭”成為中國官方推出的熱門詞彙。 《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環球時報》、《解放軍報》陸續發表文章,若干省委書記和宣傳部長也紛紛表態,支持“輿論鬥爭”、否定憲政民主。中央軍委副主席更是表示要像“堅守上甘嶺那樣”,“鉚在意識形態鬥爭的陣地上”。言下之意,輿論陣地已經失守,現在要靠網絡軍管等非常措施才能奪回陣地。或許在新一屆政府看來,輿論陣地對於信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再不收復將無力回天。只是中國在經歷了前三十年的全民洗腦、後二十年的精英反思之後,早在十年前就已進入大眾覺醒時代,現在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通過專政手段回到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
其實,在中國近六十年,不同版本的“輿論鬥爭”一直是官方主旋律。各種“整風”、“學習”等思想運動每隔幾年甚至每年都來一次,以保證黨員和大眾意識形態的高度“純潔”,只不過那個時代的大眾根本沒有自己的意誌或主見,因而每次思想“鬥爭”如同演習一樣輕而易舉大獲全勝。和威權政治不同的是,極權政治的主要體徵就是輿論和權力的高度合一:政治權力壟斷輿論工具,並生產自己的“真理”話語體系;輿論機器對全民灌輸“真理”,使其心悅誠服地接受政權統治。國家一方面屏蔽外來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用專政機器直接剪除國內的少數異己力量,以此形成“超穩定”統治。在這種統治下,全民都相信權力即真理。無論政權對你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它是不會錯的;你挨整,只能說明是你自己錯了,你只有老實悔過、痛心檢討。政治權力因代表“真理”而獲得巨大的道德資源,變得至高無上、所向披靡;“真理”則藉助專政機器的威懾力而深入人心,全民對政權合法性的理論基礎深信不疑。
中國的“前三十年”即處於這種全民洗腦狀態。 1949年後,政治異見的主力逃離大陸,剩下的小股反對力量或遭到鎮壓,或經過改造而成為“真理”話語的一部分。全國上下都毫無保留地崇拜一個人、一個黨、一種思想,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權力和真理的統一達到不可逾越的巔峰。其實這個時期仍有一批受傳統教育影響、有思想、敢說話的知識分子,但即便他們原先也對正統信仰堅信不移。 1957年“反右”前夕,中共執政才七八年時間,絕對權力即已絕對地產生腐敗和社會不滿,知識分子利用“雙百”方針對黨進行“猖狂進攻”,結果悉數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 “文革”初期也產生了遇羅克、林昭等青年反叛者,但是在全民崇拜絕對權威的瘋狂年代,反對力量如滄海一粟,無一在專政機器下留存下來。
事實上,對待這些鳳毛麟角的先知先覺者根本用不著國家暴力,只要發動群眾起來“大批判”,“六億神州”的吐沫就能把他們淹死。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導致了那麼大的人道災難,也只有黨內高層極不徹底的批評和反思。在黨內中下層和黨外,宣傳機器若無其事地照常運行;忍飢挨餓的人民對這場災難的慘烈程度毫不知情,數千萬餓死的冤魂野鬼並沒有對“偉大領袖”的形象造成一絲傷害。 “大饑荒”削弱了毛澤東的黨內地位,卻未曾貶損他在人民心中的神聖地位。正是這種格局讓他發動“文革”,利用全民對他的狂熱崇拜打倒那些因他的錯誤而獲得機會的黨內挑戰者;假如沒有前者作為土壤,“文革”充其量只是一場宮廷鬥爭,不會發展成為禍慘烈的全民運動。
“文革”之後,中國進入所謂“後極權”時代,一個標誌就是黨內外部分精英痛定思痛,開始反思造成這場全民浩劫的製度根源。進入八十年代,經濟改革伴隨著思想開放,中國社會的知識和思想結構發生全面變化,政治權力對“真理”的壟斷岌岌可危;公民社會已經開始發育,意識形態已開始經歷解構與重構。但是在這個階段,對意識形態的反思和質疑仍限於少數精英;多數民眾僅滿足於追求自己的溫飽和小康,並不關心更宏觀的政治與製度改革問題,也不具備交流信息與思想的便利手段。因此,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思想運動主要影響高校師生,並未引起社會的強烈反彈。
“八九風波”中斷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對於民主、自由、法治思想的傳播卻影響甚小。九十年代之後,關於憲政民主的各種學說仍然持續不斷進入大陸。原先國內對西方憲政制度只有粗線條理解,現在連司法審查等相對晦澀的知識細節均已成為法學常識。至少在學術界,傳統意識形態已徹底失去“陣地”,憲政民主等現代理論的知識積澱已經完成。與此同時,徵地、拆遷、分稅制、土地財政、禁止農地流轉、放任環境污染等各種借“改革”之名剝奪民利的製度開始形成並發揮作用。政改缺位造成的官僚腐敗和公權濫用直接影響了數以億計的平民百姓利益,從反面驗證了憲政民主的必要性。
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中國老百姓對發生在自己周圍發生的事件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並自覺或不自覺地和國家製度聯繫起來。以2003年發生的孫志剛事件為標誌,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復轉軍人乃至被“雙規”的官員從自身遭遇中認識到,沒有法治與憲政,自身基本利益、安全乃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破壞法治、胡作非為,但是一旦坐到被告席上,連他也不得不為自己呼籲公正審判。法治、人權、民主等憲政理念不再只是少數學者宣講的書本知識,而已經成為大眾普遍接受的常識和共識。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新一屆政府展開了大規模的“輿論鬥爭”,試圖在意識形態領域“奪回陣地”、回到毛時代。除了新一屆領導人的教育知識背景及其形成的個人思維偏好之外,這種政治左傾回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胡溫執政期間,上一屆即已形成的各種惡法產生的社會惡果全面發作,造成空前的官民對立、民怨沸騰。單面推進經濟改革的後果越來越嚴重,社會要求政治與法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讓執政者感到壓力倍增、芒刺在背。然而,實質性改革將無可迴避地觸動既得利益,執政者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觸碰的;反之,通過現有的輿論控制系統扼殺憲政民主、回歸毛時代話語則似乎代價和風險較小。於是今年“兩會”結束、權力交接完成後,就有了傳達“九號文件”、組織發表反憲政系列文章、打擊“新公民運動”、對青年教師加強思想政治控制、拘捕網絡大V、奪回輿論陣地等一系列“亮劍”行動。
當然,從其產生的效果和社會反應來看,這一行動計劃顯然誤判了中國當前的輿論形勢。 “九號文件”虎頭蛇尾,在高校傳達引起了普遍的反感,“七不講”成為教師們茶餘飯後的挪揄對象。邏輯不通的反憲政文章多以匿名發表,知名知姓的作者大都是學術圈裡名不見經傳的邊緣人物,有的根本算不上“學者”,表明官方已找不到像樣的學者為之捉刀。更重要的是,反憲政文章引起的社會反應幾乎是清一色的批判和譏諷,可見此種言論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種程度。在官方對民間發動的這場“輿論鬥爭”中,勝負早已不判自明。除了官媒的自說自話和極少數官員的被動表態之外,如今還有誰在公開支持這股反憲政逆流?事實上,官媒對憲政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不僅沒有鎮住局面,反而得罪了大批體制內學者,讓體制內的“社憲派”、體制外的“自由派”等原本不同立場的派別結成了廣泛的護憲聯盟。在這種生態下,任何學者公然站出來反憲政都是一種職業“自殺”;這麼做也許馬上就能得到“封賞”,卻徹底毀了自己在圈子裡的聲名。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哪次精英聯合抵制、社會普遍反感的“輿論鬥爭”成功過呢?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格局是六十餘年來從未有過的。在全民洗腦和精英反思階段,執政者或因自身強勢、或因順應民心,都牢牢掌控著輿論主導權,官民之間根本不存在任何“輿論鬥爭”或哪怕是實質性的對話。在毛時代,顯然一切都由他一人說了算,任何公然唱反調者都不會有好下場。有的學者對1954年憲法的上億人“大討論”津津樂道,其實那個年代哪有什麼“討論”?幾億人只有轟轟烈烈學習、領會、讚美領袖精神的份兒!鄧小平抓住人民追求自由、富裕的心理,打出改革開放的旗號,主導了意識形態潮流。 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是拉開改革序幕的重大政治事件,但其實也不是任何意義的思想或學術辯論。 “辯論”的基調早已確定,剩下的任務是找學者寫文章正面論證,反對者(當時的左派)是不會有任何機會在官方媒體發表意見、正面交鋒的。事實上,這種行事模式和現在的反憲政言論如出一轍,只不過改革開放的立場得人心,因而大批真學者願意為之效勞。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執政者當前面臨的尷尬。初看起來,新一屆領導人沒有理由不“自信”。畢竟,專政與輿論兩大武器仍然和以往一樣掌握在政府手裡。當年位高權重的“四人幫”都抓了,今天抓幾個體制外的大V算得上什麼?他們都是耍筆桿子的,而“四人幫”倒台表明筆桿子最終要聽槍桿子的。但是這種看法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打倒“四人幫”在當時就有一定的民意基礎。且不說長期被壓得抬不起頭的“臭老九”們,相當部分的普通民眾也早已厭倦了讓他們“一窮二白”的意識形態。因此,即便在極左派還掌控著輿論陣地的時候,打倒“四人幫”對於許多人來說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然而,今天反憲政、抓大V的民意基礎在哪裡呢?即便政府小心翼翼地撿了薛蠻子等幾個聲譽並不好的大V作為收拾對象,網上也出現了大量調侃和質疑,大V們更是清一色地對政府以道德瑕疵為由進行網絡整肅表達本能的警惕。時代不同了,當代中國人不僅懂得愛惜自己每天都在行使的言論自由,而且已經意識到對別人言論自由的任何侵害也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
獨立學者陳子明指出,最近的意識形態運動是在“五十年代的底色上潑墨”,但這種“底色”只是政府自己假想和力圖製造的,完全不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真實底色。當然,作為未曾清理的“文革”遺產,左派言論仍有巨大市場。反憲政逆流掀起後,“左派”確實十分活躍,據說已開始和政府聯動打擊“右派”;如果屬實,那麼當今中國已經出現了“文革”時期“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危險跡象。然而,中國“左派”看似聲勢浩大,卻終究是靠不住的,因為他們沒有經得起推敲的治國思想。除了在領土主權等外部問題上可以一時蒙蔽群眾之外,對於民生、反腐、教育、環境治理等和民眾利益攸關的國內實際問題,毛主義中找不出一個答案,多數民眾也不可能對這一套老調重彈的說教感興趣。 “新左派”雖曾名噪一時,但是其影響僅限於少數學者,政府不可能指望通過他們的鼓譟讓極左主張獲得普羅大眾的支持。除非發生戰爭或分裂等非常事件,作為一種大眾意識形態,左派已走上窮途末路。如果執政者決心向前推進改革,來自左的阻力亦無足多慮。
在經歷全民洗腦和精英反思階段之後,當代中國大眾已經覺醒並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主體思維。在今天的學者、記者、律師及普通百姓中間,支持憲政民主的“右派”已佔據絕對多數。憲政民主雖然還說不上是牢不可破的信仰,但早已深得人心。多數人或許不敢站出來主動維權,但是要把他們的思想拉回到不可理喻的五六十年代,又如何做得到?辯不過就抓人,也許能製造一時的恐怖氣氛,讓大V們眼下三緘其口,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抓了許志永、王功權,接下來又能如何?他們因言獲罪,只會收穫更多的社會同情。在國際和國內輿論壓力下,政府並不能將他們重判並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最後的結果只能是提高他們的國際與國內知名度,而自己則四處樹敵並在道義和形像上丟分。
思想的閘門猶如潘多拉魔盒,一旦打開就再也無法合攏。現在早已不是五六十年前的全民洗腦時代,領袖想要人民信什麼,人民就信什麼;甚至也不是二三十年前的精英反思時代,用專政手段就能讓少數異議者的消聲。大眾覺醒的時代已經到來,武力壓制並不能改變大眾對憲政民主的信仰。事實上,不論中共執政的原始合法性來自何處,它也不是純粹靠武力建立起來的,單純的軍事勝利並不能為它贏得廣泛的大眾支持,而國民黨之所以丟失政權,相當程度上恰恰是因為它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引起了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普遍失望和反感。在今天,國家動用武力更不可能收復思想和言論陣地,反而只能進一步自損形象、丟失民心。而在信息高度多元的網絡時代再實行語態單一的思想灌輸,顯得幼稚可笑、不合時宜。在不合時宜的方向上走得越遠,執政形象所承受的損傷越大。
面對大眾醒悟的中國社會現實,執政者有必要為體面執政做長遠打算。既然不可能扭轉憲政民主的歷史大潮,不如儘早改變“輿論鬥爭”的習慣心態,設計或接受和憲政民主更加兼容的話語體系,與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和諧相處。對於正在進行的中國經濟與法治改革而言,一個具備憲政意識的公民社會顯然是好事而非壞事。要為改革營造一個寬鬆的輿論氛圍,也必須採用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目前的“政左經右”姿態好比人格分裂,高層傳遞出相互矛盾的信號已經造成嚴重的社會困惑與對立,而官民對立無疑會造成巨大的改革障礙。其實,打破對立的鑰匙掌握在政府手裡。要讓中國改革回到八十年代初期上下齊心、官民互信的良好局面,執政者可選擇的路很寬。
反之,在打倒“四人幫”37週年的今天,還要把當年那一套搬回來,中國社會能答應嗎?
來源:微信(悅讀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