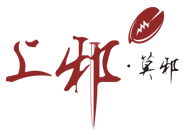不知對敏感詞語的屏蔽是不是所謂的中國特色,不過,因屏蔽技術嚴苛、僵化而鬧出的笑話之多,中國若說排世界第二,想必沒有哪個國家敢排第一(朝鮮人民表示觀眾情緒基本穩定)。最新鮮的笑話來自魔獸遊戲。 8月31日,《魔獸世界:巫妖王之怒》國服終於開通——另有台服、歐服、美服等早在2008年底便已開通,國服遲到了20個月之久。受盡煎熬的玩家發現莫名的苦難還在繼續:遊戲新增了許多屏蔽詞,如“自由”、“性感”、“激情”、“誘惑”等(此前“文胸”、“沙僧”等詞彙皆屬屏蔽之列),如果玩家註冊賬戶名中含有這些詞語,即被要求強制改名。由此衍生了一個新名詞:“目田”,用來代替被“砍了頭”的自由。
當自由成為無頭的孤魂野鬼
恐怕沒幾個詞語,比自由被閹割、屏蔽更加意味深長。
我第一個博客,建在某網站,當該網站把“乳房”列為敏感詞的時候,我選擇了告別;轉移陣地到另一網站,該網站先後將“維-權”、“憲-政”納入剪刀手之下,我欲再逃,卻發現以中國之大,竟無處不受敏感詞過濾網的毒害。區別只在於,何處尤其酷烈,寧可錯殺一千,決不錯放一個,何處相對寬容,當然,這種寬容極具偶然性,更多取決於審查者的一己之德。而且,這一人的良知擔當,無法撼動體制化之惡的一分一毫,愁容騎士惡戰權力風車過後,荼毒依然荼毒,荒唐依然荒唐。最終,擔當者被捲入極速而冷酷運轉的威權機器,或者被同化為螺絲釘,或者粉身碎骨,淪為炮灰。
就我所見,你可以把一些“三俗”詞彙設為敏感詞,可以把一些反意識形態話語設為敏感詞,可以把一些黨國要人設為敏感詞,可以把一些異議人士設為敏感詞——對於後二者而言,你禁止人們批判(讚美)他,同時則禁止人們讚美(批判)他,你卡住了民眾的喉嚨,同時則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但我從來沒見過,自由被列為禁品,置於刀口,凡從刀下過,都得挨一遭,有時斬你項上首級,有時割你臍下三寸,於是乎,言必稱自由的戰士,或成無頭的孤魂野鬼,或成被閹了小頭而只剩下(冤)大頭的太監。
由此可劃出敏感詞政治的三個歷史階段:先是生殖器官、低俗詞彙連同某些偉人熠熠生輝的姓名,不分青紅皂白,高低貴賤,一股腦被投入言論雷區的攪拌機。其次,隨時勢的惡化,風波的泛起,某些特定詞彙被發配關押於言辭的囹圄,最可怕的是,本來僅該判三個月的拘役,卻判三年有期徒刑,乃至無期,如“遊-行”、“甕-安”、“石- 首”;再如“維-權”等,被判有罪,簡直就是六月飛雪的千古奇冤,它們被迫扮演詞語帝國的趙作海之角色,時刻準備把牢底坐穿。再次,便是“自由”的淪陷。
這毋寧是一個觸目驚心的標誌,一個無以自拔的悖論。我們追逐自由,篳路藍縷,披荊斬棘,每搬動一塊石頭都要流三五斗鮮血,不曾想,才剛剛上路,作為目標的“自由”卻成了敏感詞,成了他人眼中的刺,儘管我們追逐的自由是一種權利,一種氣質,被禁止的自由只是一個狹義的詞彙。然而,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一個詞語的重量,勝過一支軍隊、一座城池。假如自由從此失踪,我們焉知什麼是liberty,什麼是freedom;我們焉知《勇敢的心》裡面華萊士那一聲撕心裂肺的吶喊不是“共-產-黨萬歲”?
被禁止永遠是一種沒有授勳儀式的榮譽
自由被砍了頭,“目田”風行天下。借用林毓生先生的話講,這乃是對中國現實的創造性轉化。記得以前有人寫文章,質問“中國人失去創造力了嗎”,現在,答案有了。不過這創造力始於壓迫,而非始於自覺。
對付敏感詞審查,國人妙招迭出。譬如用拼音以及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代替敏感詞(如世博簡稱SB),用錯別字代替敏感詞,用繁體字代替敏感詞,甚至改動版式,通用是簡體橫排,有一種軟件,可以將內容自動改為簡體豎排。所謂你有拐子馬,我有麻扎刀;你有金兀術,我有岳元帥;你有狼牙棒,我還有天靈蓋呢。見招拆招,以無招勝有招。
殊不見,網友曰:砍了“自由”的頭,還有“目田”;抽出“目田”的骨頭,還有“日日”;榨乾“日日”的血,還有“口口”。縱然將“口口”燒成灰燼,自由依然在我們心中龍騰虎嘯。而從言辭到行動,從心靈到現實,只有區區一把殺豬刀的距離。
“自由”向“目田”的成功轉化,從最具喜劇效果的角度,給了屏蔽者最犀利的一擊。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想不通,為什麼某些人會認定,屏蔽和審查是解決言論與思想問題的良方。你禁止一個詞彙,卻不能禁止它背後的精神激盪;你屏蔽你眼中的罪惡,卻不能將罪惡從此世徹底祛除。說到底,這一劑藥方的本性乃是自欺欺人,是一副狗皮膏藥,糊在了近視眼上。
“目田”的誕生,是政治近視眼們最大的苦痛。他們本以為“目田”是一根針,走近一看,原來是一顆鋒利的釘子;伸手去拔釘子,卻被扎出了血,原來釘子身上還有毒刺——這是自由之刺。自由雖掉了腦袋,雙足卻深深紮根於這塊土地。本該在胸中歡騰的鮮血,灑在了地上,化作春泥更護花。
自由被禁,恰恰折射出了敵視自由者心頭的恐懼。
其實,任何一個詞語被禁,都是它的榮耀。
鄧麗君:“為什麼會禁止我的歌曲?”
鮑勃·迪倫:“不管是什麼原因,被禁止永遠是一種沒有授勳儀式的榮譽。”
每一個漢語都在淪陷。
作為詞彙的自由被屏蔽、砍頭的同時,作為權利的自由同樣遭到公權力的非法侵犯。作家謝朝平因自費出版記錄三門峽移民史的《大遷徙》,被陝西渭南警方從北京家中抓走。罪名是涉嫌非法經營——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樣,這是一個著名的口袋罪。問題是,口袋再大,大不過公理和正義,謝朝平一未參與經營,二未以牟利為目的,非法經營的口袋,裝不了他的腦袋。
自由的淪陷絕不僅僅是一個詞語的淪陷,它能否保住頭顱,更多取決於謝朝平們的出版自由、人身自由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捍衛。如果謝朝平們的自由比枯萎的稻草還要脆弱,如果謝朝平們的合法權利之建構,乃是用竹籤代替鋼筋的豆腐渣工程,那麼,哪怕自由之頭巍然聳立,哪怕自由被寫入一個國家的最高法典,它終究是一紙空言,如斷了線的風箏,被抽乾了精血的行屍走肉;終究改變不了淪陷的命運。
數年前,網上曾流行同題作文: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今日,當自由淪為“目田”,正可重新命題:每一個漢語都在淪陷。
來源:從黃昏起飛 作者: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