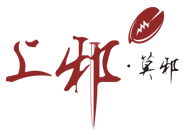中國人不一樣
中國人究竟有多麽不一樣?加州學者張隆溪曾經用了一個例子:小說家波赫士為了彰顯中國人的“不一樣”,說他在一部中國百科全書裏讀到中國人對“動物”是這樣進行分類的:
一、屬于天子的動物,二、經過防腐處理的動物,三、已經馴服的,四、乳豬,五、會尖叫的,六、寓言動物,七、無主的狗,八、屬于此類的……,十一、用駱駝細毛可畫出的,十二、以此類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遠觀貌似蒼蠅的。
波赫士當然是天花亂墜,旨在嘲弄,但傅科卻正經八百地去解讀波赫士的玩笑。他說,中國人這樣“不一樣”的思維方式顯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個文化,這個 文化專注于空間秩序;對于事物的複雜性的理解,以我們的歸類思維方式,與他們是完全無法進行命名、討論、思考的。”
中國人的“非邏輯”思維在中國哲學家圈內也是一個爭論已久的題目;梁漱冥就曾經強調過中國人重玄學的直觀思維。但是波赫士的“百科全書”如此荒謬而竟有人上當,表示“中國人不一樣”這個認定在歐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這種認定在的通俗文化裏也非常普遍。
德國南部有個旅遊景點,叫“歐州樂園”,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國”等。每個小國裏都有鮮花怒放的庭園、雅致的小橋流水。帶著民族風味的房子漆著明亮的彩色,童話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隨著甜美的音樂向遊客微笑、點頭。
樂園中唯一不屬于歐州的國度叫做“巴塔維亞之屋”(巴塔維亞是雅加達舊稱)。這個亞州小國嘛,就在一個烏七八黑的水流通道裏,陰森森的。遊客坐在小船上, 看見的是頭戴鬥笠、蓄山羊胡的蠟制中國人。怪模怪樣的亭台樓閣;鳄魚埋伏水中,長蛇盤身樹幹對遊人絲絲吐信。失火的房子裏,一個黃種人強盜高舉著尖刀正追 殺一個嘶喊的婦女。
“歐州樂園”所推出的亞洲圖像使我想起英國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個鴉片鬼的忏悔”。“忏悔”中當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對自己夢魇的描述。德昆西的夢魇有 一個不斷重複浮現的主題:“屬于亞洲的種種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誓如“在中國和印度最常見的熱帶動物──飛禽猛獸、爬蟲、奇花異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 出現。鳄魚追咬不放,他逃進“一間中國房子裏,裏頭藤制桌椅的腳突然活動起來;鳄魚那令人惡心的頭和邪惡的眼盯著我看。”但他的孩子將他吵醒,他看見孩子 “天真”的、“屬于人類”的臉龐時,不禁淚下。
“歐州樂園”所反映的不過是德昆西對歐亞文化差異成見的翻版──歐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悅無邪而安全的,亞洲則是陰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詫異而危險的。可歎的是,從德昆西到“歐州樂園”,人類已經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時光!
歐洲人固執地繼續相信“中國人不一樣”當然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們對異國風情有一種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險的異國風情較之一般的異國風情又更有刺激性。沒有了陰森恐怖的“巴塔維亞之屋”,“歐州樂園”豈不太無聊了?
兩極化的東西文化
中國人對西方人自然也有難以打破的成見。在義和團的年代,許許多多的中國農民深信傳教士會拐騙小孩,然後在教堂地窖裏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仍舊有不少人相信中國人和西方人從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上海大報就刊了這麽一篇文章:
“中國人深谙兵法,但崇尚和平;我們參戰是出于自衛,洋人則愛挑釁、好殺戮及侵略。
中國人出口他們認為最好的東西;洋人出口最能獲利的東西。
中國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馬靴。
中國人講義,洋人講利。
中國人教導子女知足,洋人教導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簡化到這個程度的思考在這裏是無須詳論的,但是同樣簡約制式的思考方式卻也同時是許多亞洲領袖津津樂道的所謂“亞洲價值”的基礎。在“亞洲價值 ”的架構裏,中國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群體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個人文化。人權觀念與個人主義是分不開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 財産,不屬中國傳統。結論就是:不能將現代西方的人權標准求諸中國。對中國要求人權的,若是中國人,就是賣國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義者。這種推論 法不僅只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愛用,西方許多自诩進步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所謂“文化相對論者”,也堅持這樣的觀點。
這樣的觀點有兩個基本問題。首先,個人主義或者人權觀念屬不屬于中國傳統,和應不應該在中國推行人權絲毫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系。馬克思主義顯然不屬于中國 傳統,卻在中國運行了半個世紀之久。女人纏足顯然屬于中國傳統,卻被中國人擯棄了半個世紀以上。所謂傳統,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實,而是不斷的突破發生。
第二個問題是,對文化的簡化就是對文化的扭曲。中國文化在時間上綿延三千多年,在空間上橫越高山大海,在組織上蘊涵數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學說, 還不去提種種巨大的外來影響,誓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斷言中國傳統中沒有個人主義,就是完全無視與儒家並列的種種思想流派,誓如極重個人自由解放的道 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嘗不是一個充滿辯證質疑、不斷推翻重建的過程?
西方文化發展形成的複雜,同樣抗拒著任何“一言以蔽之”的簡化。你說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是西方文化的胎記?哪一個時期的西方文化?文藝複興前夕或文藝複興 後?啓蒙運動前或啓蒙運動後?你說人權觀念屬于西方傳統?法國大革命前或法國大革命後?個人、自由、人權,在西方文化裏也是經過長期的辯證和實驗才發展出 來的東西,不是他們“固有”的財産。
文化,根本沒有“固有”這回事。它絕不是一幅死的挂在牆上已完成的畫──油墨已幹,不容任何增添塗改。文化是一條活生生的、浩浩蕩蕩的大江大河,裏頭主 流、支流、逆流、漩渦,甚至于決堤的暴漲,彼此不斷地激蕩沖撞,不斷地形成新的河道景觀。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當然,把文化簡化、兩極化,是挺有用的。它能夠清楚地分出“非我族類”,而異我之分又滿足了人類天性需要的自我定位與安全感。對于統治者而言,它又是一個 可以鞏固政權的便利工具。步驟一,他按照自己統治所需來定義什麽是“民族傳統”、“固有文化”。步驟二,將敵對的文化定義為相反的另一極。步驟三,將他所定義的“民族傳統”、“固有文化”與“愛國”畫上等號。這麽一來,任何對他的統治有所賀疑的人都成了“叛國者”,他可以輕易地鎮壓消滅,往往還得到人民的 支持,以“愛國”之名。
代表誰的中國人?
文化多元主義的原則是很吸引人的∶不同文化之間確實存在差異,而且我們必須尊重別人保持文化差異的意願。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症結不在“尊重”文化差異,而在“認識”真實的文化差異。好吧,“中國人說,人權觀念屬西方文化,不是中國傳統,所以不適用于中國”。在辯論適用不適用之前,有些根本的問題得先搞清楚。
是什麽“中國人”提出這種說辭?他們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是中國人的少數還是多數?如果是少數,他們有什麽代表性?如果是多數,他們持這樣的主張是基于什麽樣的曆史事實、什麽樣的哲學思考、什麽樣的動機、什麽樣的權利?
這些問題不先追究,我們何從知道他們所宣稱的“文化差異”是真是僞?如果所謂文化差異根本不能成立,就不必再討論下去了;文化相對論者也無法置喙其中。假 使文化差異是真實的,這個時侯,作為一個西方人,他可以考慮究竟該如何看待這個差異,而謹記伏爾泰的名言:“尊重不一定是接受。”作為一個中國人,尤且是 一個認識到凡是傳統就得面臨變遷和挑戰的中國人,他很可能決定:這個文化傳統壓根兒不值得尊重,只值得推翻。誰也不會否認,一整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個中國 傳統全盤重估的過程。
但是今天的中國現實又是怎麽回事呢?我們所面對的這個政權,它從來不曾允許過別人對曆史有不同的解釋;它摧毀中國傳統引進蘇聯的馬列主義;它為了政治需要 數十年不斷貶抑儒家思想,近數年來又為了政治需要而鼓吹儒家思想;這個政權把與黨的意識形態有“差異”者監禁,又對想保持“差異”的台灣進行飛彈武力恫 嚇。這樣一個政權企圖在世界上代表所有中國人說話,企圖向世界解釋什麽是中國文化傳統,並且要求國際尊重它的文化“差異”,一種由武力定義的文化“差異 ”。奇不奇怪?
托瑪斯·曼流亡美國時,記者問他是否懷念德國文化,他答道:“我在哪裏,德國文化就在哪裏。”他的意思夠清楚了:假使硬要一個人來代表德語文化的話,那麽 那一個人就是他托瑪斯·曼而不是希特勒。告訴我,哪一個文化相對論者要“尊重”希特勒所宣稱的德國文化“差異”?當然,同一個德語文化培育了托瑪斯·曼也 培育了希特勒,但是全盤接受一個由統治者片面定義的文化差異而毫不批判置疑,在我看來不是盲目無知,就是對受壓迫者冷酷漠視。
人權觀念屬不屬于中國傳統?這個問題和中國人該不該享有現代人權毫不相幹。但是在深入探究這個問題時,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就會較清晰地浮 現出來,兩者都不能以簡化或兩極化來理解和對比。尊重文化差異,是的,然而必得是真正的文化差異,而不是由統治者為了權力需要所設計出來的僞差異,或者是 為了滿足觀光客而想像出來的“巴塔維亞之屋”一類的變形差異。
我個人並不擔憂異國風情和神秘感的消失,真正的文化差異可以提供足夠的空間讓想像奔馳、好奇心深掘,而不冒扭曲的危險。扭曲一個文化固然可能點燃有趣的“創造性的誤解”,卻更可能導致毀滅性的仇恨。
來源:獨角獸資訊 作者:龍應台